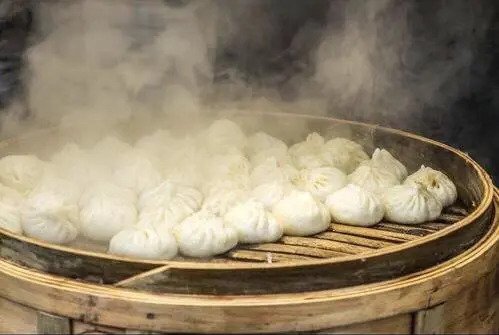07
12
沧桑五十载——写于2005年的家庭简史
我的父亲叫贾绩祥。从父亲上溯第七世祖叫贾维德,品行高尚,精通医术,闻名乡里。其事迹家谱中也多有记颂;第六世祖贾文俊,进过"国学",有11个儿子。我的高祖父贾名达,是一个热衷于"儒学"的知识分子,被家谱誉为"学实守正".我的曾祖父贾国衡以及祖父两代系单传(独子)。
我们兄弟姐妹一共六人,按出身的先后次序是:贾载钦(康)、贾载秀(女)、贾载英(女)、贾载亮、贾载明、贾载兰(女)。
父亲的文化属于旧时童生档次,毛笔字比刚笔字好。我小时候看到他用毛笔蘸着红色的油漆,把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写在门板上。我对父亲的字很感兴趣,常常有意无意盯一会。现在那字的形态还印在脑海中,很有骨架,很开阔。
我的家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完全吻合,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而后"庚子赔款".我的高祖父贾名达恰恰在这一年逝世。此后两代人一蹶不振,时间长达100余年。
到了父亲这一代,上苍隐隐传递的祖先灵气袅袅未断,时来运转,家道再兴。
父亲娶了一个好妻子,也就是我的母亲,叫张碧清。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母亲有文化。传播文化的方式不仅仅是文字,还有口头承传。我小时候,母亲常常针对儿女们的行为表现和对世事感触,说出一些很有文化的古训来。例如,当母亲听到有的乡亲对人家的儿女婚姻"打破"的时候,母亲说:"只有成人之美。"当有的人处世很吝啬时,母亲说:"为人要义气".我小时候,清晰记得在秋季的一个雨天,母亲拿出砚台和墨,叫我磨墨。接着,母亲拿起毛笔,在一块不太白的粗布上绘起花来。花绘好后,母亲又拿出针线,扎起花来。原来这是在为姐姐出嫁准备枕巾。母亲平常少语言,静穆,贤惠,善持家。其品德受到村民称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年10月1日),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物质占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的家庭在中华民国以前十分贫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后,虽经历了曲折,但情况逐渐好转。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在农村建立"互助组"、"合作社",接着建立"生产队"、"大队"、"人民公社①",概括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个公社管辖十个左右大队,一个大队管辖十个左右生产队。这些名称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刚开始走集体化道路的时候,将分散居住的家庭集中起来,实行集体劳动,集体生活。不准开"小锅灶".一个生产队成立一个伙食团,老老少少数十人或一百多人聚在一个地方吃饭。我们的伙食团在一个叫"李家老屋"的地方。我家先是从"打石场"迁到檬子垉,后来又迁到"李家老屋".由于自然灾害和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等因素的影响,1959年至1961年,缺粮很严重,死了一些人。人们偷偷开"小锅灶"了,没有受到严厉禁止,也不绝对禁止私人发展副业。我家养了一头母山羊,主要是二哥放养,因为他还不到参加集体劳动的年龄。盛夏的一天中午,二哥到山坡上将山羊牵回乘凉,路过一个满塘水的"大堰塘"时,母山羊和另外一只山羊斗角奔跑,套着山羊的绳子将二哥勒到大堰塘里,险些淹死,幸好被人救起。母山羊产了两只羔羊后,便被宰杀。是在一个深夜,几岁的我在熟睡中被二姐叫醒:"起来吃嘎嘎(即肉)"!朦胧中,她把一片"嘎嘎"塞入我口中,说"是母羊的奶子炒的".
父亲是个聪明的人,为了一大家人活命想了很多办法。除了养羊之外,他还用火药枪打麻雀。方法是,将粗糠(稻谷的壳)撒在"李家老屋"院坝里,父亲端着枪隐藏在坝里一角专门搭好的掩体后面。一群一群的麻雀先是停在地坝边的李子树上,接着飞到粗糠里觅食。轰一声枪响,麻雀倒下一片。
吃得较多的是老鼠的肉。父亲和大哥用斑竹做成压老鼠的器具,晴天的黄昏,到山上寻找方正的小石板,用斑竹做成的器具撑起石板,下置诱食。夜里,老鼠觅食到石板下吃诱饵,绊动机关,石板落下,就会被压住。第二天清晨,父亲和大哥到山上能捡到数十只老鼠。
大姐弄吃的东西体现出了智慧。她在给集体的牛割草。秋天,稻子黄了。沟壑里有田,有的地方荆棘丛生,怪石错落,灌木绿荫,比较隐蔽。大姐将黄而干的谷粒用手刷下,放在平整的石板上,再用一块薄薄的石板,压住谷粒,轻轻搓动。谷粒的黄壳破裂,现出了白花花的米。用口一吹,黄壳跑到一边,米却未动。大姐掏出手帕,将米包上,先藏在背篼的草里,最后再想另外的办法拿回家。
我当时虽还是几岁的童儿,也被饥荒逼得寻食,与小伙伴一道在刚犁过的田里泥中抠慈菇。这褐色而圆圆的东西有甜甜的爽味。我们还抓稻田里的蚱蜢,在柴火里烧熟后吃。冬天种下的马铃薯,浇了粪尿的,我们几个小伙伴偷偷刨了几瓣出来,在风篓火里焖熟了充饥。一年春末,社里从地里收的豌豆堆放在伙食团住地的走廊里,我们几个小伙伴神不知鬼不觉钻进去,偷食豌豆,后来被发现,中午饭没有发给我们(是一个桶形的小瓦钵蒸的大米,量很少)。我们眼睁睁看着别人吃饭。但后来,不知是出于吓唬我们还是有人说情,把饭给了我们。
有的人饿得吃糠壳,拉不出屎,要旁人拿起竹钎掏。被掏者痛得惨叫连连。
我们吃过一次"观音米"—一种到很远的地方去挖回的一种仿白色粘性强的泥巴。由于营养不良,我差点死去。
1962年,全家人终于熬过了极端困难时期。虽然仍然是集体劳动,但伙食团解散。父亲说"有钱难买独家村",全家搬迁到原来曾经住过的"青竹山"上。这里处于全队地理位置的边缘,每天出工干活比别人要多走不少路。房子依托的地方,是开山打石后留下的平地。住居四周是竹林。整个地势是一个斜坡,前面较缓,后面很陡峭但有竹木遮掩。屋子右侧100多米处,有一口横卧的"8"字形堰塘,是唯一的水源。门前竹林边有一条顺山直上山梁大路。山梁如龙之脊,比山下平缓。翻过山梁下行约一里处,是被九十年代撤消了的"革岭公社"驻地。
伙食团下放后,生活渐渐好转。能勉强维持生存。国家允许家家户户种自留地。给每人大约划一分地,不能划田。自留地可以弥补粮食不足,人们抽一早一晚的时间,种得很认真。同时,还容许家家户户养猪、养鸡鸭等。自留地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全部土地划分到户。
我们所在的大队叫"柏木大队,"八十年末更名为"柏谷大队"(因本县院庄乡有个大队也叫"柏木"),公元2005年春,柏谷大队建制被撤消,合并到"黑马大队".大队没有撤消的时候,下辖六个队,我家属于第六队。连着我队土地的是黑马大队的一队和二队。一队的户主(男人)全部姓贾,没有他姓。1984年,"生产队"的称谓一律改为"组"(如我们队称"第六组"),"大队"一律改为"村".原来只有大队支部书记,改后既有书记,又有村长;书记由乡(镇)党委任命,村长由村民选举。"公社"组织构架上实行"党政分设",名称一律改为"党委"和"人民政府"②。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乡(镇)长兼任党委副书记。是形式上的分开,内容并未分开,政府在党委的领导之下,统一开展工作。
生产队时的劳动形式是全队的劳动力同时出工,集体劳动。根据工种的性质,有时分工,有时不分工。例如挖土的时候,所有的劳动力都使用锄头,不用分工。如搞农田基本建设,有的打石头,有的抬石头,有的砌石头,就必须分工了。同一劳动有分开干的时候,如挖土(采取抓阄的方式选择地块),但这样的时候不多,因为质量不高。集体劳动中虽有偷懒的,但绝大多数比较自觉。物质分配形式采取"基本口粮"加"工分"的办法。前者按人口计算,后者按劳动力出勤所记的"工分"计算。一般一个全劳动力为10分。这样,劳动力多的家庭分到的口粮自然要多些。"童工"也可以到队里干力所能及的劳动,当然记的工分要少些。
我的父亲有一些捍卫集体的精神,不怕得罪人,比如有的人侵吞了集体的财产或损害了集体的利益,他会发言反对。他说话直来直去,呼喝时声音宏亮,队里有的人给了他一个外号—"吼天狮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当了生产队队长,但由于他性格太刚,受不了气,干了一年多便辞去了。
大哥读书的成绩较好,但因为我家人口多,劳动力不足,父亲要大哥弃学参加生产队劳动,以养活一家人。大姐、二姐自然也未上学(并相继于六十年代中期出嫁)。
父亲是允许二哥读书的,但他读不进去,自动放弃了。
1965年,我进了本大队的学校—柏木小学。教我们的老师叫薛本勋。以现在一般的小学老师水平衡量,薛老师的水平较高,写得一手好字,学校面壁的口号就是薛老师自己搭架子,然后攀登上去写的。内容是:"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每写一个字都要移动一次脚手架。他还购来了一些连环画本,每周都安排时间讲解,课余时间去借也可。我后来爱好读书、爱好文学就从这里开始了。那时读书的学费和书本费太便宜了,至今尚记得,一般在3.60元左右。那时的小学、初中分别读4年、3年,但小学与初中之间,还要读"高小"两年。小学升入"高小"是全公社(全乡)统考,1969年,我考入了"高小".一天,传递通知的老师也是我后来读"高小"的班主任柯大生来到我家,远远高喊我的父亲:"贾老汉、贾老汉,你的少爷考上了"!
这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处于高潮。父亲、大哥都被卷入了"派性"斗争,碰巧和薛本勋、柯大生以及后来的初中班主任刘蔚清(男)老师是一个派,叫"红云"派,对立的派叫"1127".1969年,发生了万县地区所有市、县的"红云"派武装进攻云阳县的"1127"派(称"九县一市,攻打云阳"和"文攻武卫,解放云阳")。以"1127"的失败而告终。派性仍然在继续,1970年,父亲在所谓"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掌权的"1127"批斗。先是在生产队里一个叫"檬子垉"的公房里开斗争会。时间是冬天,我去了,但没有进会场,蹬在室外靠墙壁的石头上。我听到一个人领头喊 "揪出‘516分子’伸向柏木的黑手"等口号。第二年夏天,很热,夜里在露天里睡。父亲把我摇醒说:"娃儿,你是读了点书的,他们还在整我,你看有没有办法?"我睁开眼,看到母亲也坐在旁边。我小小年纪,懂得什么。有略通文墨的人给父亲壮胆,不要怕,可以申述。父亲将申述材料寄到县上,反而更加激怒了仇恨父亲的那伙人,于是又把他叫到公社大会堂批斗。 "一打三反"运动结束后,父亲再没有受到批判。
二十一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农作物的所有种子全部是传统种子,所有家畜家禽也是传统品种,农药、化学肥料也几乎没有,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虽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而综合生产力水平极低。传统水稻亩产只有200公斤左右。所以粮食和肉食品都不丰富,只能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吃干饭的次数很少。红苕、小麦、马铃薯、玉米占的比例不小,还有胡豆、豌豆等。吃肉的次数比吃干饭的次数多,每年年末宰一头猪(但有些人家没有宰年猪,主要看家庭主妇女能不能干),当然是为了过年。但这头猪肉实际上要管一年。一块一块腌了盐,挂在房屋楼上。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母亲常用腌盐后晒干了的菜加少许肉丝烧汤,然后再拌入米面粉,做成羹,味道可口。土质条件好、管理好的生产队,比我们生长队的生活要好一些。
那时劳动力虽然管得很严,但允许个别人离开农业生产,或就近或外出搞手工业。大哥跟着一个叫李明发的裁缝师傅学徒弟,地点就在革岭公社那个地方,二哥到湖北省宜昌等地学泥瓦匠。但要给生产队缴公积金,每天缴0.10元左右。1972年冬,家境好了一些,大哥找回的钱有些节余,因此改造了房屋,将原来的茅草房变成了瓦房。虽然只有两间,但堂屋的开间很宽。左边煮饭和放柴草的两间屋子和右边的猪、羊圈,仍然是茅草屋。后来大哥分家另住,在左边挨着堂屋又修起一间瓦房。
1973年夏,我初中毕业,本来考上了高中,但因公社有几个人对父亲有意见,卡住了我入校的大门。只好干农活。犁过田,抬过石头,当过石匠。1974年,大队建立面粉加工厂,招工人三名,我有幸入选。这段时间,我五更早起,先锻炼身体,然后苦读中医著作。
集体劳动,必然伴随着文化交流。人们一边劳动,一边摆故事。我脑海里储存的许多故事和学的知识都是在集体劳动的时候。《石猴出世》(就是写的《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的故事就是一个叫贾少其的人边挖土边讲的。他还能讲很多民间故事,如"红红绿绿一只鸡,一枪打了飞进山里,不知是你的还是我的。"还讲当时美国人侵略越南,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天某日又打落了一架美国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飞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华国锋接班,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打倒,称为"四人帮".1977年夏,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入大学中专实行全国统一考试。临考前半个月的一天夜里吃晚饭时,父亲说:"广播里天天都在说考试,你读书时成绩好,去报名试一试".母亲也鼓励我去。那些年,读书要走"后门",已死了进学校门的心,对广播里的宣传不相信,许多人都持怀疑态度。所以对父母的话没有积极回应。父亲又说,"明天就到学校你们老师那里去问一下情况,看还可不可以报名,反正不花本钱。"第二天,我到了学校。老师说:"可以报名呀!"于是就报了名。一考竟中了。
农村的变化随之而来,生产管理上,实行作业组,即将一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分成两个以上组劳动,目的是提高劳动积极性。我所在的队分为两个组,父亲是其中一个组的组长。这个办法对促进生产有一定作用。1978年暑假回家,看到漫山遍野的玉米即将成熟,昌茂如林,丰收在望。
八十年代初,国家提出对农村的生产管理实行"水统旱包",即将土划分到户自己经营,田仍然实行集体耕作。1983年,国家将田也划分到户③,称为"双层经营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家庭经营,与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以农户为经营单元的方式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农民相对自由了,除了组或村开会外,农民活动的空间完全由自己安排。自然,交给国家的"农业税"也以家庭为单元上交了。渐渐地,农民除了交税而外,还要交 "植物保护"、"畜禽防疫"等名目逐步繁多的费用,人平税与费高达100元以上(有些地方更高),如遇集资修公路或办其它公益事业,则多得多。须知,农民种粮不仅不能赚钱,而且还赔本。市场粮价往往低于成本价。一些地方政府因强行收费而逼死了一些农民。中央政府看到这一问题,于2003年决定:逐步在全国免收农业税和一切费用。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配套措施还有,撤消一些乡政府,合并一些"组"与"村".
九十年代以来,小学至大学的收费逐渐增高,到二十一世纪初,小学每学期(半年)收费150元—300元不等;初中每学期收费300元—600元不等;高中(县级中学)每学期收学费600—1000元不等;大学每年收费6000元—18000元左右不等。一个大学生读完四年,各种费用一般需要60000元以上。各学校收费的标准不一致,这里只记载了一个大致的数目,不怎么精确。以上说的费用,只是一次性缴的学费,还不包括平常多种名目的其它收费。由于大学收费太高,有的家庭贫困的父亲为了子女上大学而长期偷偷卖血;有的学生用的钱是自己的姐妹卖身的钱。国家和各级政府虽不断出台控制教育乱收费的政策,但到目前(2005年)为止实际没起作用。高额的学费已经超过大多数国民的承受能力。除了教育普遍受到沉重的高额收费而外,排列第二位的高额收费就是医疗费(医院卖出的药品价高出市场价很多)。教育和医疗系统的乱收费已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被舆论称为"行业不正之风".当然"行业不正之风"不仅仅表现在教育、医疗系统,可以说是全社会的,是腐败行为的"伴生物".
二十世纪八十代初以来,袁隆平研究出的杂交水稻开始推广,使亩产比原来增加两倍,达500公斤以上。这是科学技术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时代开始研究遗传科学产生结果。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家畜家禽遗传杂交技术也得以广泛推广,提高了肉产量达40%左右。农药、化肥也基本满足了生产的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形势。但八十年代末以后,科技推广的水平基本停留在八十年代初的水平,没有突破性进展。而广泛性的、大规模水利建设、改良土壤(造梯田等)在二十一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就基本停滞了(主要是"单干"的原因),仅少数地方实施了比较典型的水利工程和改土工程(是国家拿了钱不得不搞)。
农业生产工具还没有根本改变,虽然一些地方使用了收割机、脱粒机、抽水机等农用机具,但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牛、犁头、耙、锄头、镰刀。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了电,公路网罗逐渐形成,人们与外部的交流方便些了。特别是电子技术的发展,农村几乎家家都有了电视,这自然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从1977年开始,国家逐步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只准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城市基本上做到了,但农村一些地方,一对夫妇一般都生了两个以上子女。政府发现有超生的,对国家干部职工,要开除公职,对农民等对象则实行高额罚款。
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国家逐步在全国范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前面提到的"户营"是农村基本政策的一个改变。随之不久的八十年代中期,国家允许甚至提倡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打工人数不断增加,形成潮流之势。主要是到广东等沿海、沿边地区和大中城市。许多地方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外出,留在家里的是老、弱、病、残、幼。大哥的五个子女全部到广州等地打工。
在异乡当国家公务员的我回乡探望亲人,脑海里留下了一幅图画:不缺粮了,绝大多数农户都改造了房子,山上山下的植被比原来好多了,农民自由了。年轻人几乎都外出打工了。大哥二哥都改造了房子。二哥甚至离开老屋,在另外的地方新建住宅,使老屋逐渐凋闭。但是,社会公益事业停滞不前,落后的迷信等封建文化复活,神秘文化活动猖獗,宗教组织在不断蔓延,偷鸡摸狗的事时有发生。大哥被迷信坑害过,父母在老屋子养的鸡和农具被盗。小偷多次前来,一次,老母亲将小偷反锁在屋里。小偷趁母亲去叫人的时候,破门而逃。红白喜事铺张浪费现象也较严重,打牌赌博比比皆是。这些情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是没有的。乡村看起来不仅很萧瑟,而且被复活的各种封建文化和非健康的精神现象笼罩着。
1999年1月19日24时,父亲患肺癌逝世,享年73岁。葬于大哥、二哥家屋外"大坵田"左角下大路旁。行政辖地为云阳县盘石镇黑马村贾家大湾与原柏木村相连的地方。
不幸的是,二哥贾载亮外出打工,于2005年5月10上午11时许在四川省宣汉县中心水库煤矿矿井里劳动时牵引拉煤车时被煤撞击胸部,导致肺脏重伤,医治无效死亡,年仅53岁。在达州市火化后回家乡,葬于黑马村紧临贾家大湾的小山,即贾载玉住宅附近。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继承前人优秀的精神,正确认识一段时期的真实历史。后浪推前浪,奋发向上,艰苦创业,拨开迷雾,披荆斩棘,勇于拼搏,开辟新的天地,做出新的业绩,为家族、民族、国家增光添彩。
注释
①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把这一调整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方的不同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自此,人民公社开始比较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
②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
③ 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肯定了以"双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形式。在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93%,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包干到户。
(写于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