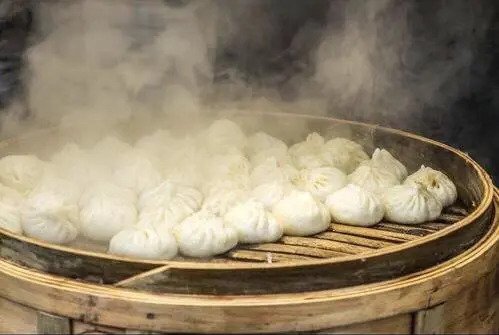02
02
风中的芭茅
我一贯顾念着那些倔强的芭茅草,在风中,在漫天彻地的孤苦里。每一簇都直直卓立,向着天和多数往还无量的季候。
芭茅,神似芦苇。仅仅芦苇是那么大度的意象,静立水边,站成了一个低眉怕羞的美。在水一方的斯文,从《诗经》的弦外之音缓缓流淌了千年。彷佛与水有关,必然傲视散播、脉脉厚情。芭茅则是山峰的孤魂,成群而生,却各人人孤单,举目皆是,而不敢问津。
我坐在去往异地的车上,高速公路的两旁莫得光景,除了无限的山。扫数的山都在上昼的阳光下静默,连云亦然。风,在山间穿梭。那些山的绿色的底色上竟有一簇簇的红。深色的红,像流浪在绿色之上的云。为什么有血色?车子飞驰而过,扑面而来的红垂垂清澈,竟是神似芦苇的芭茅,从车窗前疾速跑过。细高的秆上血色的穗子,像风中的部分面旗子。
昂首,环视,扫数的山上都是芭茅。远望,似朵朵强大的淡色花,傲向天穹。山,都是低矮的山,全都默默着。扫数的杂树乱草都是大舒畅的绿色,或浅或淡。石头从淡淡的绿色里探出面,像孤苦的岛屿。茅草恣肆地在山间成长着,每一丛茅草既群居又独处。修长的叶子显出坚挺的绿,细秆上是血色的穗子,乱发大凡在风中飞行。
人,是一棵有念念心田的芦苇。芦苇临水而居。再高的天际和再远的云,都在身边的水面悄悄铺展。对一只水鸟或一缕风,好吧倾诉的标的那么多。莫得人心田成为一棵芭茅。带着更多对土地、乱石的倔强,在荒山野岭间沉寂,成了风中的心魄。满山的芭茅,在山中、在干燥的沟渠边,成长是一大米即兴的部署。莫得采取,我心田到了秋天,这么多的芭茅,皆首如飞蓬,相向而观念。等风来或雨至,就把接下来的全体,交给了工夫。
芭茅很有用。嫩芭茅可食,及枯黄可用来行为农家作念饭的燃料。但芭茅叶片四周尖利如刀片,经常会划伤皮肤,是以那些在墟落沟渠边的簇簇芭茅老是让人侧目而视。幼时,外婆家左右的小径上,有一蓬活力勃勃的芭茅。我心田折下那些修长的茎秆,举起那血色的穗子奔驰。绿而修长的芭茅叶,霎时如一把把刀绵亘在面前。我用力扒户口叶片,只感应皮肤火辣,在迫近那些茎秆时,奋勇一折。待我从芭茅丛中跑出,才发明胳背上多处划伤。我的手里拿着血色的穗子,而那被折了茎秆的芭茅彷佛还举着刀,咱们两虎相斗。血色的穗子滑而冰凉,在我的伤痕轻扫过,未几久就掉了活力,而我也自此阔别芭茅了。
上学后,家与学塾相距甚远。通衢远而平展,小径近而逶迤。偶尔,爸爸也会带我走小径。走小径需翻过尽是松树的小山头,风从林子深处而来,每一棵松树都轻轻摆动,轰鸣声似风浪迭起的海洋。穿过野外好吧望见山头的人家,野外极端的小沟边长满了芭茅。我骑车途经小沟边的田埂,没来得及下车,就栽到了沟里。我倒在干燥的沟渠里,抬眼满是雄伟枯黄的芭茅,天际仅仅芭茅丛里的一抹蓝色,竟那样弥远。人人行车压在我的身上,我躺在一个田野的沟里和多数芭茅为伴。这异样的观念角没宝石半响,爸爸就把我拉起来了。一阵风过,大蓬的芭茅轻轻流动,枯黄干涸的质料,发出沙沙的声音。
我经常梦见己方在野外奔驰,大片的芭茅,或绿或黄,或荣或枯,在乡野目田地成长。枯黄了的芭茅,偶尔人人然地兴废,偶尔只需一把火。火焰吞吃了坚挺的叶片和蓬乱的穗子,眨眼只剩下焦黑的土地,显露了沟渠素来的式样。那些一望无垠焦黑的沟渠或小径,在所有这个词冬天沉默莫名,只等着春风渐暖,芭茅抽出嫩枝,把新的绿色涂抹上去。以是,年光就逐步远去了。
主义地是一个小县城,司机停驻车等人。我告急下车,心田去顾念顾念那些一块招日光的芭茅,竟毫无脚迹。高速路口边的野外,绿不到边。水池里,夏季活力盎然。满池荷叶,蜂涌着高举的血色荷花,随风娇贵地摆动。在跑过那些山峰的时辰,芭茅就仍旧不见了。
那些随风而逝的草木,还在无人留心的山峰沉寂成长。春生秋枯,人人生人人灭。风吹过,只是仅仅吹过少许浅浅的器械。扎根下,就爱着眼下的土地和头顶的天蓝。我心田芭茅必然不会念念心田。